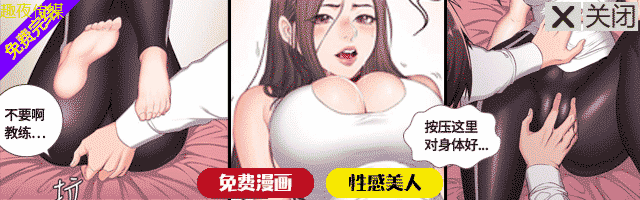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母欲的衍生】(2)(第3/5页)
百度搜索新暖才文学网,即可找到我们,网址为拼音缩写https://www.xncwxw3.com
(前面加https,http可能无法访问),
即将改版,更多精彩小说请点击"首页-分类-其他小说"
书架功能已恢复,可注册登录账号
袍也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没出现过。
那种「温水煮青蛙」的进程,似乎被那个「咚」的一声给强行按了暂停键。
我心里像是猫抓一样难受,看着她在屋里晃动却包裹严实的身影,那种「看
得见吃不着」的煎熬比以前更甚。
但我也没敢再造次。我知道,这时候再往前一步,可能就会炸雷。
时间就这样在闷热和拉扯中,滑到了八月底。
知了的叫声开始变得凄厉,那是夏末的绝唱。
就在我以为这个暑假就要在这样的冷战与隔阂中结束时,那个男人回来了。
那天下午,一辆满身黄泥的大货车停在了巷口。
父亲李建国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得很突然,既没有提前打电话,也没有带什么礼物。他就像是一
个匆匆过客,带着一身的烟味、汗馊味和长途跋涉的疲惫,一头撞进了我们母子
俩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里。
「妈了个巴子的,这趟活真不是人干的!」
父亲一进门就把沾满油污的背包扔在沙发上,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脱掉了上衣,
露出黑黝黝的胸膛和一肚子肥肉。
母亲正在摘菜,看见父亲回来,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一种明显的错
愕,紧接着才是一种职业性的、属于妻子的忙乱。
「咋这时候回来了?也没说一声,我都没买肉。」母亲站起来,在围裙上擦
着手。
「买啥肉?随便弄点吃的就行,累死老子了。」父亲大马金刀地往竹椅上一
坐,竹椅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那哪行,你这在外面跑半个月,不得补补?」母亲说着就要往外走,「我
去割点肉。」
「别去了!别去了!」父亲不耐烦地摆摆手,「就下碗面条,多放点油。吃
完我得睡一觉,明天一早还得走。」
母亲愣住了,脚步停在门口:「明天就走?这么急?」
「有个急活,去广东,老板催得紧。」父亲闭着眼,仰在椅子上,满脸的灰
土,「这一趟运费高,为了这个家,拼了呗。」
母亲看着他,眼神里的光彩黯淡了下去。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
后只是叹了口气:「行,那我去下面。」
那一晚,家里出奇的安静。
父亲确实是累坏了。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大碗面条,连澡都懒得洗,只是
拿湿毛巾擦了擦身子,就倒在了卧室的床上。
不到五分钟,震天响的呼噜声就传遍了整个房子。
「呼——呼——」
母亲收拾完碗筷,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一会儿。
她身上穿着那套保守的棉绸睡衣,背影显得有些萧索。
她本来也许期待着点什么,哪怕是几句贴己的话,或者是夫妻间的那点事。
但父亲的呼噜声像是一盆冷水,浇灭了她所有的念想。
他把这个家当成了旅馆,把她当成了不用付钱的服务员。
「妈。」我坐在堂屋看书,叫了她一声。
母亲回过神,转头看着我。
灯光下,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眼神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处安放的空虚。
「你爸累了,让他睡吧。」她轻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你也早点
睡,后天就要开学报到了。」
那一晚,隔壁没有传来任何旖旎的动静。
只有父亲那不知疲倦的呼噜声,像是在嘲笑这个家里另外两个人的失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父亲就走了。
正如他来时一样匆忙,只留下了一屋子的烟味和还没散去的浑浊气息。
随着大货车的轰鸣声远去,巷子重新恢复了宁静。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巷口发呆。晨风吹起她的衣角,勾勒出她丰腴
的身形。
她转过身,关上门。
那一刻,我感觉她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塌下去了一块。那种因为
父亲短暂归来而竖起的「贤妻」架子,瞬间散了。
「走了?」我问。
「嗯,走了。」母亲语气平淡,没有太多的悲伤,「跟个打仗的似的。」
她走到沙发上坐下,整个人瘫软在里面。
那种前几天为了防备我而竖起的「警觉」,在巨大的空虚感面前,似乎也变
得不那么重要了。
「向南啊。」她看着天花板,喃喃自语,「明天你也要走了。」
「嗯,明天去学校报到。」
「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守着这破房子。」母亲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从
未有过的脆弱,「守活寡似的。」
这三个字,像是一把锤子,敲在了我的心上。
我看着她。她那件棉绸上衣的扣子,因为瘫坐的姿势而崩开了一颗。
这一次,她没有立刻去扣上,也没有拉衣服遮挡。
她只是闭着眼,任由那一抹白腻在空气中暴露着。
下午,我们开始收拾行李。
高三要住校了,这是学校的规定。
母亲跪在地上,帮我整理箱子。她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叠好,塞进去,又把几
瓶牛奶和一罐辣椒酱塞在缝隙里。
「这被子薄了点,过阵子天凉了我再给你送厚的。」
「内裤袜子要勤洗,别攒着一堆带回来。」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像是在用这些琐碎的话语来填补心里的空洞。
我蹲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侧脸。
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流下来。她今天没化妆,眼角的细纹很明显,但这并不影
响她那种熟透了的风韵。
「妈。」
「咋了?」
「你自己在家……注意身体。」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我。
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那种要把我推开的警惕,反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
不明的依赖。
「知道了。」她笑了笑,伸手帮我理了理衣领,「你在学校好好读书,别给
妈丢脸。我就指望你了。」
她的手指触碰到我的脖子,温热,粗糙。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那晚她给我按头时的触感,想起了她大腿内侧那个红印,
想起了她在水雾中仰起的脸。
「妈,我会经常回来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避开了我的视线,低下头继续收拾箱子。
「回来干啥?车费挺贵的。半个月回来一次就行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看到了她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
第二天,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那条老巷子。
母亲一直送我到车站。
烈日当空,她打着把遮阳伞,站在站台上。
「到了学校打个电话。」
「知道了。」
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隔着玻璃,我看见母亲依然站在那里,那一团丰腴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
显眼。
她看着车子启动,挥了挥手。
车轮滚滚向前,把那个家,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充满了汗水、红花油味和未
遂欲望的暑假,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但我知道,这并没有结束。
相反,距离只会让渴望发酵。
在学校那些枯燥的夜晚,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梦里,那个总是虚掩着的卫生
间门,那条晾衣绳上飘荡的内裤,还有母亲那声似有若无的「冤家」,将会变成
最猛烈的毒药,腐蚀着我的理智。
等到下次归来,那扇门,我一定能推开。
回学校的大巴车里充斥着一股劣质皮革和汽油混合的味道,车载电视里放着
聒噪的喜剧小品,但我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像是有无数只苍蝇在飞。窗外的景
色飞快倒退,那个有着潮湿苔藓味道的小县城,那个有着昏黄灯光和母亲身影的
老房子,正在离我远去。
高三的生活对于旁人来说是紧迫的、争分夺秒的战场,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
说,却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监牢。学校的围墙很高,上面插着碎玻璃渣子,把那一
帮躁动的青春期野兽死死地圈在里面。教室里永远弥漫着一股粉笔灰的味道,混
合着几十个男生挤在狭小空间里发酵出的汗馊味、胶鞋味,还有那种因为长期焦
虑而产生的口臭味。这种干瘪、粗糙、充满了雄性荷尔蒙却又无处宣泄的环境,
简直就是地狱。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盯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函数公式,视线却总是无法
聚焦。那块墨绿色的黑板在我眼里慢慢晕染开来,变成了一片深沉的紫色——那
是母亲那件真丝吊带睡裙的颜色。数学老师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这道题
是必考点!注意辅助线的位置!辅助线画不好,这题就废了!」他的唾沫星子在
阳光下飞舞,而我的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划动,画出的却不是什么辅助线,
而是一道道圆润、饱满的弧线。
那是母亲弯腰拖地时,臀部撑起布料的弧度;是她坐在竹椅上,领口垂落时
胸脯受到重力牵引而坠出的轮廓;是那天她生病时,汗水顺着脊柱沟蜿蜒而下的
路径。
我像个瘾君子,在极度匮乏的环境里,依靠着记忆里那些偷来的片段苟延残
喘。那颗名为「欲望」的种子,在这枯燥压抑的日子里,不仅没有因为距离而枯
萎,反而因为「禁欲」而疯长成了燎原的野草,死死缠住了我的理智。我看书,
书上的字会变成母亲那件针织衫上的纹路;我看窗外的树叶,会想起她洗头时湿
漉漉的发丝贴在白腻脖颈上的样子。
我开始有意识地放纵这种走神。或者说,这是一种病态的报复——报复这枯
燥的生活,也报复那个把我「赶」回学校、试图用「正途」来规范我的母亲。
这种状态很快就反应在了成绩上。起初只是作业的一两处错误,然后是随堂
测验的及格线边缘。我看着卷子上鲜红的叉号,心里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慌,反而
涌起一种隐秘的、扭曲的快感。这红叉不仅仅是分数的扣除,更像是我手里捏着
的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拴着那个在家里守活寡的女人。我知道,只有这根线动
了,她才会痛,她才会慌,她才会把全部的注意力从那些琐碎的家务中抽离出来,
死死地钉在我身上。
九月底的月考如期而至。那几天的天气闷热得反常,像是要把入秋前的最后
一点暑气都蒸发出来。考场里的风扇呼呼地转着,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物理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只扫了一眼大题,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就断了。
那些滑块、斜坡、摩擦力,在我眼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线条。我握着笔,手心里
全是汗,脑子里全是母亲那天在卫生间里,水流冲刷过她身体的画面。我想象着
那水流的温度,想象着如果我是那水流……
我大概只写了一半,剩下的时间,我就那样趴在桌子上,在草稿纸上反复写
着「妈」这个字,然后又一个个涂黑,涂成一个个漆黑的墨团,像是一个个深不
见底的黑洞,要把我吸进去。
成绩出来的那个下午,班主任老王脸色黑得像锅底。他是个快五十岁的中年
男人,地中海发型,平时对我们还算客气,但这次显然是动了真火。
「李向南,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办公室里很安静,其他老师都去上课了。老王把我的物理卷子狠狠地拍在桌
子上,那声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回荡,震得我耳膜嗡嗡响。
「四百八?总分四百八?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